吴堡芽子炒碗托
○宋红红
陕北有一种美食叫碗托,因在碗中成形而得名,由陕北盛产的荞麦制作而成。它有多种吃法,镇川麻辣肝子碗托、吴堡刀刀碗托都很出名。而在吴堡游子的心中,最经典的当属那一盘芽子炒碗托。
在吴堡,豆芽叫作芽子;家里长豆芽,叫作生芽子。这个词一出口,豆芽生机勃勃的形态就活灵活现地展现了。小时候,一到冬天,家家户户都会生芽子,生芽子原料当然是用吴堡山山峁峁上长出的一颗颗绿格莹莹的绿豆。选出颗颗饱满的豆子,提前用凉水浸泡、沥干,倒在一个大瓷盆里,盖上一个高粱秆制成的盖子,上面再压一块石蛋,冬天还要放在热炕头,盖一个棉袄才合适。一天一换水,不出三天,绿色的豆子被泡胀得圆鼓鼓、绿莹莹的。仔细端详,已经有白色的小芽顶破豆皮,露出小尖头。第四天、第五天,小芽从弯弯的到越长越长,越长越壮。等豆芽脑袋的绿壳一抖落,一个个脑袋胖乎乎、身材修长、白格森森(方言)的豆芽就可以吃了。总记得,睡梦中的早晨,奶奶在给豆芽换水,总会说一句:“咦——又长了,看这芽子长得俊了不?”我总是惊奇,咋生芽子跟生孩子一样。只见半盆豆子一天比一天多,最后满得都要溢出盆外了。
冬天温度低,生好的豆芽好储存,除了日常吃,最主要是要在过年时炒碗托用。
豆芽生好,就要准备做碗托了。制作碗托用的杂粮——荞麦,也是一种很独特的作物。《神农书》里记载,荞麦是“三伏天”过后播种,至霜降时节就能成熟的粮食作物。所以七八月都可以种荞麦,而且荞麦不挑地皮,山间地头只要下种,就可以开花结果。小时候走在田间,没几步,就会发现一片繁茂的荞麦地。荞麦开花非常好看,纤细的红茎秆上点缀着一簇簇白雪似的小花朵,花瓣洁白,花蕊粉嫩,配上爱心模样的一片片绿色叶子。如果此时迎着山坳吹来了阵阵凉风,湛蓝湛蓝的天空,你会发现一朵朵云儿和一片片荞麦花海一般模样,惬意极了。大片大片的荞麦花开,如云似海,实在是美不胜收!
荞麦成熟了,褪去黑色的壳,露出泛着粉红的荞麦仁,荞麦仁三棱的,仔细一瞧,每个面和叶子一样是爱心形状的,明月,爱心,好浪漫的一种食物啊!
做碗托,荞麦仁要提前一天泡好,第二天再装在一个纱布做好的小袋子里,开始揉搓。揉的时候倒点水,不一会工夫,绵密白皙的面浆在妈妈的双手间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。面浆好了否,以挂勺为准。面浆做好后,舀在一个个宽口碗里,放锅里蒸,蒸熟揭开锅盖,就要拿筷子快速搅拌,待放凉食用。那一系列动作,在妈妈的手里如行云流水,碗托刚出锅的清香,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刚出锅的碗托,叫滚糊糊碗托。叫法是根据碗托的形状而来的,虽然看起来是糊糊,但是热热的刚出锅的荞麦香气非常浓郁,口感绵密筋道,加上调料的香——熟芝麻盐、韭菜、扎蒙油、醋、蒜水,再淋上一圈辣椒油,美绝了。这是吴堡当地早餐的主角,一般人要吃上三碗,才肯罢休。暖暖的,昨夜的酒也醒了,今晨的饭也吃了。
晾凉的碗托,则更筋道。除了凉拌,在吴堡最经典的吃法当属芽子炒碗托。每年过年,最后一道菜,就是芽子炒碗托。大锅里倒油,爆出葱蒜香,芽子下锅翻炒几下,注入灵魂汤汁——醋水,最后把切成两厘米厚的碗托条倒进去翻炒,撒少许调料,倒少许生抽,不能多,多了就掩盖了食物原本的味道。当那一股醋香弥漫在窑洞里的时候,春晚的旋律就开始了,当芽子炒碗托端出来时,全家老小已经迫不及待了。
芽子炒碗托,还经常出现在各个戏场和集会上。记忆中,离戏场老远,最先闻见的就是芽子炒碗托的醋香、荞麦香,还有豆芽的清香。其次才听到咿咿呀呀的粉末旦角的唱戏声。人还未到,心已经流连到某一个卖碗托的摊位前了。似乎每个集会上都有一个“凤莲碗托”,卖碗托的每一个“凤莲”都长得白白净净、干净利索,笑着问你要辣子不?芽子炒碗托配上发面油旋,最好不过了;对,再加一罐健力宝。这样,戏看完了,集赶完了。回家的路上,一个个饱嗝,都是芽子炒碗托的味道了!
如果你来吴堡,一定不要错过那碗最具烟火气的芽子炒碗托。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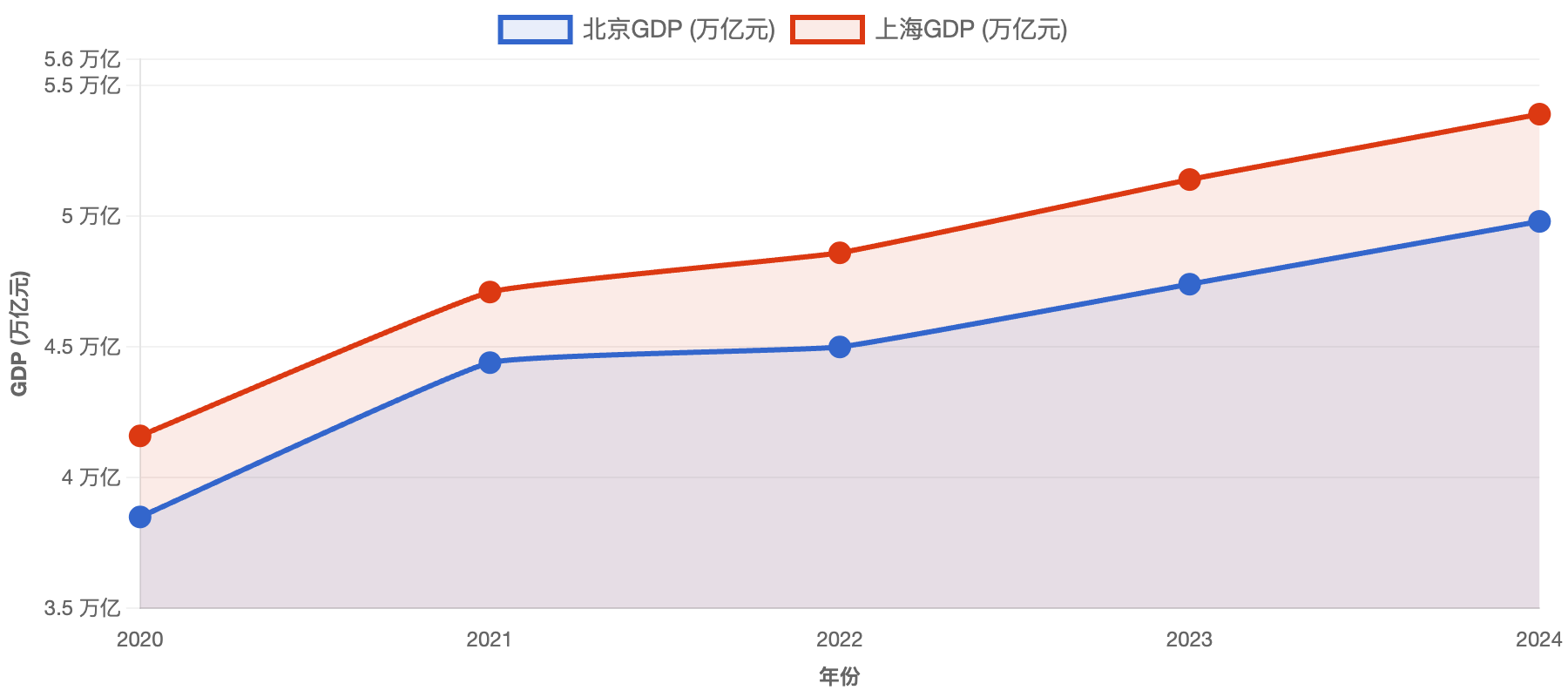
评论